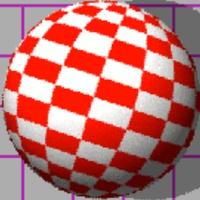道格·恩格尔巴特是如何成就“所有演示之母”(the Mother of All Demos)
编译自:连线杂志(Wired)最近的一篇文章:How Doug Engelbart Pulled off the Mother of All Demos,这篇文章摘自Adam Fisher 写的《Valley of Genius》这本书。
道格·恩格尔巴特(Doug Engelbart)是第一个真正制造出我们现在可能很熟悉的电脑的人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他曾在海军担任雷达技术员,随后来到硅谷。在他自己看来,他是一个“天真的流浪者”,但硅谷的某些东西激发了他的远大理想。恩格尔巴特的想法是,未来的计算机应该针对人类的需求——沟通和协作——进行优化。他认为,计算机应该有键盘和屏幕,而不是打孔卡和打印输出。它们应该增强而不是取代人类的智力。因此,他召集了一个团队,建立了一个工作原型:联机系统(the oN-Line System, NLS)。与早期的努力不同,NLS不是军用超级计算器。这是一个通用工具,旨在帮助知识型员工更好更快地工作,这是一个有争议的想法。让非工程师直接与计算机交互被认为是轻率的,甚至是乌托邦式的颠覆。然后人们看到了“演示”。
道格·恩格尔巴特:我终于拿到了博士学位,开始教书,并申请了斯坦福研究院(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, SRI),我想如果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我探索这个“增强”的想法,那就是那里。当时斯坦福还是一所小型工程学院。惠普成功了,但仍然很小。到1962年,我写了一篇关于我想做什么的描述,第二年我开始拿到钱。
鲍勃·泰勒(Bob Taylor,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[DARPA]局长,该机构资助了恩格尔巴特的工作):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SRI的人,提出了一项名为“增强人类智力(Augmenting the Human Intellect)”的提议。我喜欢这个提议中的想法。我最感兴趣的是,他将以一种人类从未有过的方式来使用计算机:用他的话来说,就是“增强人类的智力(augment human intellect)”。这是我能想到的最清晰的描述。我和这家伙取得了联系,他来华盛顿见我,我们帮他签了一份NASA的合同,这比他以前得到的资金要多很多。这让他和他的团队开始这项研究。
恩格尔巴特:我有钱做一个研究项目,试图测试不同类型的显示选择设备(display selection devices),就在那时我想到了鼠标这个想法。
比尔·英格利什(SRI总工程师):那发生在1963年。我们与NASA签订了一份合同,评估不同的显示指向设备(display pointing devices),所以我收集了不同的设备——操纵杆、光笔——道格在他的一个速写本上画了一张“鼠标”的草图。我觉得这看起来很不错,所以我拿着它,让SRI的机械车间为我做了一个。我们把它包括在我们的评估实验中,它显然是最好的指向装置。
泰勒:“鼠标”是由NASA资助创造的。还记得NASA宣传“菓珍”(Tang,饮料)对文明世界的巨大贡献吗?嗯,有一个更好的例子,但是他们不知道。
恩格尔巴特:我们必须自己制作计算机显示器。你买不到它们。我想1963年花了9万美元。我们只能从零开始。显示驱动器是一块3英尺乘4英尺的电子设备。
史蒂夫·乔布斯(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):道格发明了鼠标和位图显示。
巴特勒·兰普森(Butler Lampson,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科学教授):SDS 940(用于演示)是我们在伯克利的一个研究项目中开发的一个计算机系统,然后我们慢慢将其变成产品。恩格尔巴特在940上建造了NLS。
泰勒:道格和他的团队能够使用现成的计算机硬件,通过软件改变你能用它做什么。对人们来说,软件比硬件更难理解。硬件,你可以拿起它、触摸它、感受它,看看它是什么样子的,等等。软件更加神秘。道格的团队确实进行了一些硬件创新,但他们的软件创新真的很了不起。
比尔·帕克斯顿(Bill Paxton,增智研究中心[Augmentation Research Center]的同事,参与了“演示”):记住——把你自己放在当时的情况。这是一个小组,一整个小组,共享一台功能大致相当于……(计算机)。如果你用iPhone来衡量计算能力,那相当于千分之一的iPhone。这个小组的10个人使用的是iPhone千分之一的计算能力。太疯狂了!这些人创造了绝对的奇迹。
唐·安德鲁斯(Don Andrews,增智研究中心的另一位同事):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,基于道格的愿景,我们正在努力做什么。我们正在寻找快速原型化新用户界面的方法,因此构建了一个框架,一个基础结构,我们可以非常快速地在其上构建一些东西。我们知道事情会很快发生变化,本质上我们是在自我激励。
艾伦·凯(图形用户界面的先驱):在编程中,有一个广泛的理论认为,一个人不应该制作自己的工具(one shouldn’t build one’s own tools)。这是真的——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那上面了。另一方面,如果你能制作自己的工具,那么你绝对应该这样做,因为可以获得的杠杆作用是不可思议的。
帕克斯顿:在团队中,每个人都在使用相同的工具,并且每天都在使用它们,开发工具的人就坐在使用工具的人旁边——这是一个非常紧密的循环,导致了非常快速的进步。
恩格尔巴特:到1968年,我开始觉得我们可以展示很多戏剧性的东西。我有一种冒险的感觉,好吧,让我们试一试,结果往往以失败告终。
泰勒:在那些日子里,在这些计算机会议上,总是有一些小组讨论攻击交互式计算的想法。原因是多方面的。他们会说,“嗯,太贵了。计算机时间比人的时间更有价值。这是行不通的。这是白日梦。”因此,包括计算机构在内的绝大多数公众不仅无知,而且会反对道格试图做的事情,他们也反对交互式计算的整个想法。
恩格尔巴特:不管怎样,我只是想试试。我发现美国信息处理联合会(American Federation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)会议将在旧金山举行,所以我们可以做些什么。我向组织这个会议的人发出了呼吁。幸运的是,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会议将在12月举行,我在3月开始准备,或者更早,这是一件好事,因为,他们对我们非常犹豫。
泰勒:即使在从事交互式计算工作的社区中间,也可能存在某种排序。总是存在的。当时,在这个“演示”之前,道格的团队很可能处于那个排名的最靠后。
帕克斯顿:当时90%的人认为他是个疯子,认为这种“交互”的想法是浪费时间,这种想法不会有什么结果,真正好的东西是人工智能...有几位像鲍勃·泰勒这样的人接受了这个想法。最终,这个想法进入了施乐PARC,然后苹果(Apple)接管了世界。但是,在那个时候,道格的声音无人问津(Doug was a voice crying into the wilderness)。
泰勒:道格和我在1968年初讨论过做这个“演示”,我强烈鼓励道格去做。他说,‘这将花费一大笔钱。我们将带着这个巨大的显示器,我们将在旧金山和门洛帕克之间提供在线支持,这将花费一大笔钱。’
凯:基本上,当他们向泰勒询问做这件事的时候,泰勒说,‘听着,花你需要的钱,但是不要少花——要足够的冗余,这样事情才会真正有效。’
泰勒:我说,‘别担心。ARPA将支付这笔费用。’ARPA是在艾森豪威尔(Eisenhower)的鼓动下由国防部创建的。我们的想法是成立一个机构,支持高风险的研究,不需要繁文缛节,这样我们就不会像(前苏联的)人造卫星出现时那样再次感到惊讶。
恩格尔巴特:那时候,我们只是在好朋友的基础上和你互动。我应该告诉他们多少?我告诉他们的够多了,这样他们就知道我想做什么了,他们实际上是在告诉我,“也许你不告诉我们更好。”我们投入了大量的研究资金,我知道,如果它真的崩溃了,或者有人真的抱怨了,可能会有足够多的麻烦,可能会毁掉整个项目。因为我们滥用了政府的研究经费,他们将不得不切断我的联系,取消我们的资格。我真的很想保护赞助者,所以我可以说他们不知道我们做的事情。这就是我们之间的默契。事实上,比尔·英格利什从来没有让我知道这个项目到底花了多少钱。
凯:我相信ARPA花了175, 000美元(1968年)用于那个“演示”。今天大概是一百万美元。
恩格尔巴特:很多钱。
泰勒:比尔·英格利什为那个“演示”付出很多。
恩格尔巴特:事实上,如果没有比尔·英格利什,这个“演示”永远不会成功。不知怎的,他是得心应手去安排事情的。
凯:即使是好的想法也是便宜和容易的,但是我们也有比尔·英格利什和他的实干家团队,他们能够把这套想法具体化。
英格利什:从SRI到市政中心(Civic Center),这是一个挑战。我是说那是30英里以外!我们从电话公司租了两条视频线路。他们建立了一个微波链路:两个信号发射器在SRI大楼顶部,接收器/信号传送器在天际线大道(Skyline Boulevard)的卡车上,两个接收器在市政中心。电缆当然从两端进入房间。那是我们的视频链接。回到过去,我们有两条专用的1200波特线路:当时的高速线路。自制调制解调器。
恩格尔巴特:我们需要这台视频投影仪,我想那年我们从纽约的某个机构租了它。他们不得不把它空运来,并派一个人来管理它。
英格利什:我们用了一台Eidophor(大图像投射器),一台瑞典投影仪,一台复杂的机器。那是一台大机器,差不多六英尺高,是一台弧光灯投影仪。它所做的是将弧光聚焦在一面球面镜上。镜子是用挡风玻璃刮水片擦拭的,在每一帧之间,涂满了油,而电子束实际上是把图像写在了油里!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方法。
凯:那里不只有一台Eidophor,有两个。它们都是从NASA借来的。接下来的问题是,‘如果我们的冗余不起作用呢?’
斯图尔特·布兰德(出版了《全球概览》):就带宽和可靠性以及所有其他方面而言,他们正处于这项技术所能达到的极限。
凯:然后,他们去了Ampex公司,这家公司刚刚开始进行高分辨率视频录制,他们买了一台巨大的Amex记录器,他们在上面做了整个演示,它在直播的时候一直在运行,以防有什么事情出错。
恩格尔巴特:有盒子可以播放两个视频,你转动一些旋钮,你可以淡入淡出一个视频。有了另一个,你们可以把视频放进来,你可以用一条水平线或一条垂直线把它们分开。很容易看出,我们可以做一个控制台来运行它。
凯:比尔设计了整个系统,设计了整个显示系统和其他一切。比尔是鼠标的共同发明人;他并不是二流人物。
恩格尔巴特:比尔用所有这些装备在后面搭建了一个平台。
凯:恩格尔巴特很有魅力。比尔是工程师。
恩格尔巴特:四种不同的视频信号进来了,他把它们混合,投射出来。这是我们从未听说过的先例。
凯:这个“演示”的规模——简直难以置信。
帕克斯顿:我是新人,几乎一无所知,所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《全球概览》的斯图尔特·布兰德是我们的摄影师。谈论某人来放松气氛!
约翰·马科夫(John Markoff,科技记者):斯图尔特真的是一个人,比任何人都更能指导迷幻药物从精神和治疗走向娱乐。他是反主流文化的载体。
布兰德:恩格尔巴特办公室的一些人一直在关注我在Trips Festival上做的事情,等等。他们认为我可能会给他们计划的“演示”带来一些制片价值,或者关于如何展示的知识。所以,他们邀请我过去。
凯:那时候,《全球概览》实际上也是一家商店,就在SRI街的对面。
布兰德:我记得我走过去想,这可能很有趣,甚至可能很重要。当我看到他们在做什么时,一切都显得非常壮观和显著的。当然,你会想做他们用计算机做的那种事情!他们邀请我参加了他们策划这个“演示”的几次会议。
凯:斯图尔特也参与其中。我是在一次聚会上通过比尔·英格利什认识他的。《全球概览》杂志的很多人都在那里。
NLS于1968年12月在旧金山公民中心布鲁克斯大厅的全国计算机会议上首次亮相。当灯光亮起时,恩格尔巴特坐在舞台上,身后投射着一个巨大的视频屏幕,一个鼠标触手可及。然后,在所谓的“所有演示之母(the Mother of All Demos)”中,恩格尔巴特展示了他的计算机可以做什么。
布兰德:我参加了展示本身的“演示”部分。
帕克斯顿:布兰德在摄像机后面,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镜头对准监视器,然后放大,这样图像就填满了整个屏幕。他让这个伟大的反馈循环运行起来。这真的很酷——非常迷幻。这基本上就是幕后的情况。
布兰德:我曾经是一名专业摄影师,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说,‘哦,太好了,你来操纵相机。’这基本上只是点和焦点。但是“演示”令人震惊。
恩格尔巴特: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看到鼠标,看到轮廓处理,看到超文本,看到混合文本和图形,看到实时视频会议。
凯: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想法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,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过滤,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试图自动化当前思维模式的东西,而是我们和这项新技术之间应该有一种放大的关系。
恩格尔巴特的NLS终端有一个屏幕、键盘、窗口和一个鼠标。他展示了一种编辑文本的方法,电子邮件的一个版本,甚至是一个原始的Skype。对现代人来说,恩格尔巴特的计算机系统看起来相当熟悉,但对于一个习惯打孔卡(punch cards)和打印输出的观众来说,这是一个启示。计算机可能不仅仅是一台数字计算机;它可以是一种通信和信息检索工具。在一个90分钟的“演示”中,恩格尔巴特打破了军用计算的范式,为那些已经聚集在硅谷的嬉皮士、自由思想家和激进分子提供了一个未来的愿景,这个愿景将推动未来几十年的技术文化。
泰勒:观众席上大约有1000多人,他们都惊呆了(blown away)。
安迪·范·达姆(Andy van Dam,布朗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):看到这个专业系统如此丰富和复杂,我大吃一惊。这是一种超凡脱俗的体验,事实上,我无法让自己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。
泰勒:没有人见过有人用那种方式使用计算机。这真是了不起。结束后,全场起立为他鼓掌。
凯:我们喜欢的是它的范围。恩格尔巴特真的很厉害。
兰普森:非常壮观。
布兰德:从那以后,我看过很多演示,并参加了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演示,等等。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危险的事情,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胆的事情。我们从未对活动进行过全面的排练;有部分彩排,但是人们看到的是实时的即兴创作。我不认为人们意识到这是即兴创作,但这就是即兴创作。这给了这个可能成功的事情一种额外的高保真的品质。我不得不说,道格在管理所有这些方面非常出色,他是媒体本身的大师,并且已经成为他所操作的完全拼凑在一起的通信系统的大师,他在舞台上完全镇定自若。当比尔对着耳机小声说:‘停几分钟,我们无法得到……’不管那是什么东西坏了,道格就会停下来,谈论点别的事情,直到他得到消息说:‘好了,我们继续。’我们很幸运,度过了那一天。
范·达姆:当时,我与泰德·纳尔逊(Ted Nelson)合作开发了我们的第一个超文本系统,团队由三名兼职本科生组成。我们当时正处于类似工业革命中使用锤子和凿子的阶段,用汇编语言进行编码,我们非常擅长这个。但是,这些人发明了机床。他们构建工具来“构建工具”:整个递归的“引导”思想简直令人难以置信,从系统本身开始,通过增加人类的智能一路向上。直到现在仍在影响着我们。
乔布斯:我们人类是工具的制造者。我们可以设计一些工具来放大这些固有的能力,我们拥有惊人的能力。所以对我来说,计算机一直是心灵的自行车(a computer has always been a bicycle of the mind)。
肯·凯西(Ken Kesey,作家):这是迷幻药之后的下一件事!
乔布斯:这让我们远远超出了我们固有的能力。
帕克斯顿:那天观众中有很多人深受其影响,走出去说,‘我该怎么做?’